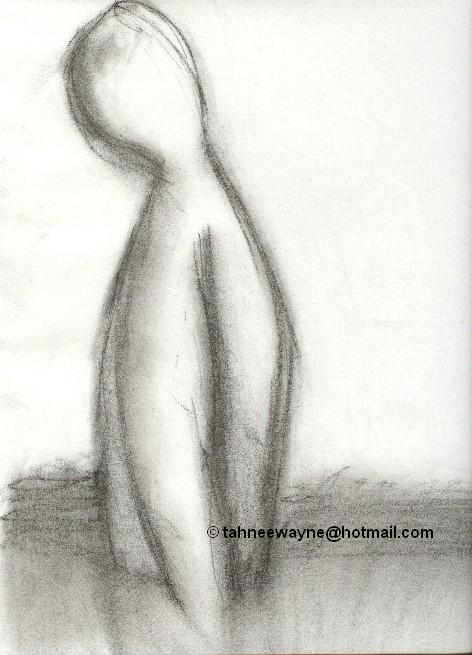天啊!今天是我所作实习的研讨会开幕的日子,然而,只是一天,我真的已经要向他们彻底投降了!说句不够体面的话,我真是服了这些来自“大草原”的人了。
其 实征兆在昨晚接机回酒店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些所谓的旅游部门高级官员眼睁睁的看着宾馆的门童一个人推着行李车,辛辛苦苦的从车上往下搬运一件件厚重的 行李,又主动搭着电梯推着车挨个运到他们的房间门口。官员们坐在房间里,坦然地指着自己的行李,意思是让门童再帮他们拎进房间。爸妈平时都说我不勤快,可 那时我站在门童身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行李都到门口了,都不肯搭把手接一下,懒死!那可是您自己的东西!”这还不算,竟然连小费都没给我们可怜的门 童。这可都是官员啊!这点基本礼节都没有吗?还是说成心欺负我们中国人?!
今天早上开准备会之前半个小时,我把最后一份文件夹送给从南非 来的一位女士。敲开房门,出现了一张睡眼惺忪的脸,问我现在几点了,我说差五分九点,然后她睁大了眼睛:“Morning or night?”我慌……时差不至于倒成这样吧?我顿时意识到她必定要迟到了,一边要她抓紧时间“沐浴更衣”,一边向已经到达会场等待的其他国家官员解释会 议的延误。其中赞比亚来的一个叫Charles的人问我难道她不知道会议时间吗,我说了她的特殊情况,没想到他却开始责备我,说什么是我们通知的问题,是 我们的失误,既然我们办了这个研修班就应该负责任之类种种。拜托,她睡过了关我什么事啊!这些人时间这么充裕,各自习惯不同,根本不可能委托酒店作 morning call,那我还得在梦里挨个通知:“早上啦,起床啦!”?!接着在会上,我们组委会的主任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位先生上来就问:“什么时候给我们 发现金补助啊!”晕……想钱想疯了吧!这哪是我们在援外啊,简直是请来一债主!
下午去首都博物馆的时候,偏偏当时馆内没有英文讲解,所以 组委会决定由我来担任馆内讲解一职,就因为我是这里面唯一一个去过的人,而且还是当初陪美国人去的。讲就讲,咱北京自己的东西还是难不到我的。可渐渐的, 他们问的问题越来越让我迷茫,什么:"What is buddhist?", "Why you use animals to represent good thing?", 还有"Why do you also have temples?",他们甚至不知道18世纪的时候中国也曾被西方列强侵略过,甚至不知道Forbidden City是干什么用的、在不在北京!如果他们是日本人,不懂英语我还能理解,可这些人都是来自非洲英语国家的,平时他们的交流语言就是英语!最后一个问题 把握彻底打败了:“What is dynasty?”……我突然意识到,按照他们这样的知识储备,我刚才的所有讲解等于没讲,换句话说,所有那些我自认为很有价值的内容对于他们来说完全 make no sense!
参观完首博,这些来自12个国家官员们一致要求要找地方去买数码相机,听组委会的同事们说这些从非洲来的人 都觉得中国的电子产品便宜,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要买。为了保险起见,OC决定带他们去国美。没想到他们回来之后竟纷纷抱怨说东西太贵,extremely expensive。我索性问他们他们想象中的便宜是什么样的价格。得到的答案让我哑口无言:他们想用400多卖iPod,用5000左右买 Toshiba的笔记本,用900块钱买Sony的DV……最后我只有两句话来回答他们:“Are you kidding me?”和"It's impossible."。每次谈话后,我总习惯性的问一句:“Anything else?”并且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something else,不但要浪费掉更多的时间,更要忍受更多超级变态的问题。举个例子吧:“Can I buy a car here and have them send it to my home?”下一句话就是:“Do you think 1,000 or 2,000 USD will be enough to buy a car?”……各位亲爱的读者,不用我再多加什么评论了吧?
回到办公组我跟主任说的第一句话就 是:“这差事太挑战心理承受能力了!”这还没完,九点半,刚刚安顿下来,又接到餐厅打来电话:“你们这儿有三个赞比亚的人要吃晚饭,你们过来看看吧。” Yuck!都什么时候了!六点半所有人都在等他们开饭,现在九点半才回来,还要吃饭?这要是我的人,绝对一句话甩过去:“吃什么吃!饿着!”其中一个男的 好像喝高了一样,跟我一位同事姐姐胡说八道,真佩服这姐姐的涵养,还一直跟他应付着,以我的脾气,转身走了得了,跟他这儿废什么话啊!处理完这仨赞比亚 人,回到房间,妈妈打电话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是否顺利,我的回答是:“总算见识什么叫蛮夷之地出来的人了!”虽说这话有点重,可是我心里的确是这么想 的。同事们倒是挺镇静,安慰我说:“见识了吧?去年就这样,我们都快习惯了。”几天疲劳战术之后我本计划要早点休息的,无奈义愤填膺,一定要写点什么才痛 快。
刚刚接到组长从机场打来的电话,说已经接到了从塞舌尔来的官员了,是一个特别绅士的白人,身份好像不一般,要我们马上在酒店这边做好 准备。还说写完东西就去睡觉,今晚到的人由同事去安排就好了,连衣服都换掉了,结过电话同事姐姐手忙脚乱,又是准备文件夹,又跑去前台确定房间,还不忘嘱 托我:“快换衣服,拿着东西到楼下!”拿着外交护照的人果然不一般,不但中国驻塞使馆打来电话要求对这个人特别关照,而且塞舌尔政府好像也很重视,尽管人 家本来业务繁忙都不想出席了,来了,也依然要处理很多事务,传说中还包括会见塞舌尔驻中国大使等等。看来大家的紧张也是不无道理,否则,姐姐也不会拉着我 大半夜跑到宾馆门口等人。更何况,这于我,简直就是缓和我心中的中非关系的重要桥梁!或者说,是让我们在与其他官员挣扎到近乎崩溃时支撑我们坚持下去唯一 的希望。
现在又到了半夜,姐姐还在旁边跟excel和扫描仪奋斗,有了动力果然不一样,加班加点也在所不辞。可惜我的热情有限,连续熬也迟早要垮掉,还是早早休息才好。